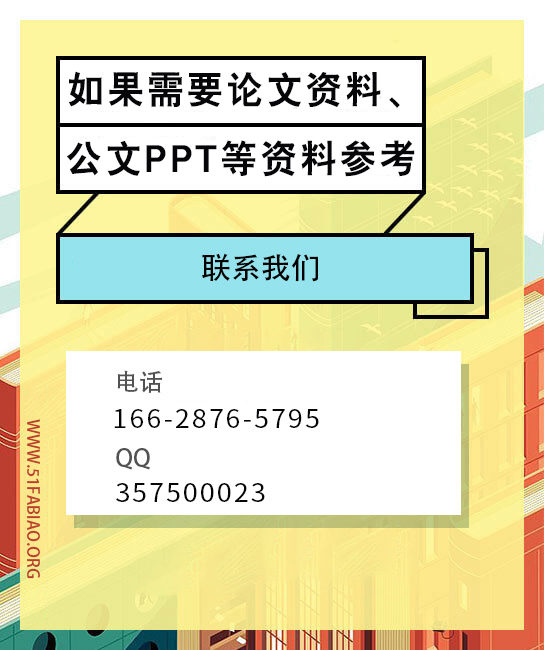罗莎·卢森堡是一位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她在第二国际中的独特地位, 她与列宁之间的历史论争, 以及她的那些充满预见性和前瞻性的政治哲学思想, 不仅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 同时也激发了我们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社会发展的起起落落、胜利与挫折, 反复地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其实现革命性转折的道路和方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的多样性等问题, 重新提上历史日程。而卢森堡的政治哲学由于是在社会- 历史的宏观视野下去探讨国家、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规则、规范和价值, 它们的性质、它们的历史与社会的渊源等, 因而其所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定的适用意义, 其中所体现出的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展望未来的整体理论视野, 对我们解决今天出现的新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卢森堡的政治哲学不是抽象的思辨理论, 其理论和方法就存在于她对现实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和本质的整体分析中; 而这首先得益于她对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永远从总体的、全面的、深层的、内在的观点去看待一切问题。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直接源于马克思, 但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 马克思与卢森堡在坚持社会总体性的共同前提下对各个组成部分的强调程度又有所不同。在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整体中, 卢森堡针对当时盛行的经济决定论和教条主义, 着重强调了实践的和主观的方面。在此意义上, 卢森堡实际从上层建筑方面对总体性作了重要补充。事实上, 卢森堡的一个有价值的思想就在于, 她认为资本主义体制潜藏着非理性的、破坏性的巨大力量; 这种力量如果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得到释放, 如果人们不主动选择社会主义, 就必将滑向灾难的深渊, 而威胁到全部人类。“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在野蛮中灭亡”, 这句名言所凸显的正是一种顾全整体的政治选择的重要性。因此, 她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信念绝不意味着她主张宿命地、消极被动地等待胜利,因为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崩溃的形式加以引导, 它决不会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社会主义前景, 而会是全部阶级、全部人类的灾难甚至毁灭。即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可以想象的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为社会主义提供一切条件, 实现社会主义仍然需要主观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 卢森堡政治哲学的精义就在于“从一种外在于人、与人无关的政治转向一种对人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政治” (Bronner, p. 46) ,而这种转变的前提在于人们的主动参与和行动。
行动是重要的, 但行动也可能是盲目的, 而只有具有阶级意识的行动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卢森堡由此提出她的阶级意识理论。在她看来, 社会主义革命与以往种种革命的本质区别就在于, 这是一场有阶级意识的、有群众心理基础的、大多数人的自觉的革命。因此,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群众心理”, 或者说, 这种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内培育和加强但注定要在制度之外得到满足的无产阶级的自我能动认识, 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装饰品, 而是决定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现实因素。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中必须具有阶级意识的要素, 卢森堡提出了她的另一个著名口号: “革命不是‘制造’的”,因为在进行或发动群众运动时, 群众的心理成熟程度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长期形成的, 这决定了革命本身也是不可事先规定和计划的。
卢森堡政治哲学的总体性方法和阶级意识理论对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前者而言, 卢森堡并未过多地论述总体方法本身, 她所做的是将它运用于自身的理论实践, 贯彻于实际的理论斗争; 在她那里, 理论与实践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且当时更重要的任务是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促进实践的发展, 但这有时也会限制她对方法的系统表述。而在卢森堡这里还主要体现为一种具体运用的总体性方法, 经过卢卡奇的明确的理论阐发, 终于正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同卢森堡一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和政治上对总体或整体概念的强调, 反映了他们对第二国际机械经济决定论的反对态度。卢卡奇明确提出,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的范畴。这个概念来源于黑格尔, 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它意味着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全面的理解; 不能以单纯的自然因素来解释历史, 而是要将主体与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 突出人类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这样, 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的具体运用, 经由卢卡奇的系统阐发, 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体性”构成了这一思潮的中轴线。
卢森堡的阶级意识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则表现在, 他们在反思无产阶级运动时认为, 资本主义之所以未在20世纪20年代的混乱局面中崩溃, 正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形成它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应肩负的潜在历史使命这一充分的阶级意识。同时, 卢森堡的阶级意识理论还突出了群众的心理因素和文化建设, 强调了阶级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成, 从而为后来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革命转向微观生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契机。而且, 在卢森堡看来不言而喻的是, 只有具备了总体的观念才能使群众达到对资本主义整体的认识, 从而才能树立起正确的阶级意识, 因此总体性是阶级意识的基础。这一观点无疑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
卢森堡政治哲学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思想是她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理解。卢森堡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她那篇颇有争议而又极具价值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 她在其中力求发现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的真实内涵。
长期以来, 人们总是习惯于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给社会主义下定义, 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 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和它的基本价值关怀来对它加以界定。在此意义上, 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突出强调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首先, 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强调与她把人看作总体是分不开的, 即人不仅有经济需求, 而且还追求精神和政治的满足。在她那里, 政治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起码是同等重要的; 这与她对民主的总体性看法也是分不开的, 即只有当社会主义民主是作为整个阶级的事业时, 它才是真实可行的。
其次, 在卢森堡看来,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应该是一种能够包容不同观点, 强调思想交锋, 从而能够使自身真正得到维护和健康发展的民主和自由。卢森堡意味深长地写道, “自由始终只是指具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这不是为了对‘正确性’表示宗教狂热, 而是为了使政治自由中一切有教益的、健康的和纯净的因素都建立在这种实质之上, 并在‘自由’变成特权的时候指出自由的作用。” (《卢森堡文选》下卷, 第500页注1) 卢森堡在这里强调了政治生活中批评、监督、建议的自由。如果一个政权是健康的, 这种自由只会促进它的巩固和发展, 接受、贯彻这种自由正表明了这个政权的强大和勇于改进与前进的决心与信心; 只有虚弱的政权(俄国在1917年的确是虚弱的) 才会害怕和限制这种自由。而且, 卢森堡的目的还在于, 使民主的真实内涵不要受到所谓的“民主”组织或“民主”执行者的官僚主义的、专制独裁的歪曲。也就是说, 使民主摆脱不良组织的束缚, 因为民主、人民的代言机构由于没有那些旧的民主形式的制约而不再为民主、为人民代言, 演化为僵硬的、冷漠的、独立的甚至是腐化的官僚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 卢森堡要求通过公共生活本身的磨砺, 实行最大限度和最广泛的民主和舆论监督。总之, 她所重视的是政治生活中的实质内容, 她所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目的, 而不是表面的“民主”或民主“假象”, 而且这种民主的核心之一就是反特权。
第三, 卢森堡并没有费力去对“一般”民主进行一种平庸的捍卫, 并不否认实现民主有其特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基础, 也没有忘记民主的阶级性和具体性, 以及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本质区别。但同时, 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 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又不是绝无可取之处: 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它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它的民主形式或外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从政治国家走向社会整体的历史趋势。因此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不能彻底断裂。事实上, 传统的民主本身还有一切社会共有的一方面, 即作为一种理想和价值, 作为对社会基础和最终目的的人的权利的维护。在这层意义上, 她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和表决的民主, 而更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民主和精神上的自由, 强调民主对人本身及其精神自由发展的尊重, 强调民主生活对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日常意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即民主对人的精神解放的作用。在她看来, 后者决定前者。
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阐发与她对俄国革命缺乏民主的未来前景的隐隐担忧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卢森堡的批评可能违反需要一个高度集中制政权的那一时期的历史现实, 但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卢森堡的警告是有道理的。今天人们普遍承认民主、自由的价值, 即民主和自由在人们看来是值得追求和实行的, 因而民主和自由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尤其是在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 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阐发也许不应再被仅仅视为一种理想, 而是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性。卢森堡所开创的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 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
要理解卢森堡的政治哲学思想, 她与列宁之间的历史论争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总体而论, 他们在一些大的原则性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 并从自身的实践出发, 各自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森堡最后甚至为了这
无忧论文库
- 市场调查与预测论文
- 工商管理论文
- 战略管理论文
- 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 市场营销论文
- 酒店管理论文
- 电子商务论文
- 组织行为学论文
- 信息管理论文
- 成本管理论文
- 企业问题研究论文
- 客户关系管理论文
- 媒体管理论文
- 风险管理论文
- 旅游管理论文
- 技术经济学论文
- 财务管理论文
- 企业文化论文
- 管理论文
- ERP论文
- 国际商务管理论文
- 网络营销论文
- 信用管理论文
- 会展论文
- 运营管理论文
- 物业管理论文
- 生产管理论文
- 企业管理论文
- 品牌管理论文
- 质量管理论文
- 社区管理论文
- 团队管理论文
- 渠道管理论文
- 销售管理论文
- 企业社会责任论文
- DBA工商管理博士论文
- 微观经济学论文
- 宏观经济学论文
- 国际贸易论文
- 金融证券论文
- 农业经济论文
- 经济管理论文
- 投资论文
- 政治经济学论文
- 中国经济论文
- 经济学理论论文
- 产业经济论文
- 新经济学论文
- 社会经济论文
- 房地产论文
- 区域经济论文
- 低碳经济论文
- 农村经济论文
- 发展经济学论文
-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
- 经济师论文
- 国际关系论文
- 行政管理论文
- 文书
- 政治学论文
- 电子政务论文
- 民主制度论文
- 社会主义论文
- 资本主义论文
- 马克思主义论文
- 邓小平理论论文
- 毛泽东思想论文
- 司法制度论文
-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论文
- 党建论文
- 军事理论论文
- 公务员论文
- 会计论文
- 审计论文
- 成本会计论文
- 电算化会计论文
- 管理会计论文
- 会计理论论文
- CPA论文
- ACCA论文
- 税务会计论文
- 会计制度论文
- 财务会计论文
- 会计实习论文
- 会计论文发表
- MPACC论文
- 会计师职称论文
- 内部审计论文
- 审计风险论文
- 英语翻译学论文
- 英美文学论文
- 英语语言学论文
- 英语其它论文
- 商务英语论文
- 英语教育论文
- 小学英语教学论文
- 初中英语教学论文
- 旅游英语论文
- 计算机英语论文
- 英语教学论文
- 中外文化差异论文
- 英语毕业论文
- 英语论文范文
- 英语文学论文
- 跨文化交际论文
- 临床医学论文
- 护理医学论文
- 中医学论文
- 医学技术论文
- 医药学论文
- 外科论文
- 呼吸论文
- 妇产科及儿科论文
- 泌尿科论文
- 骨科论文
- 皮肤病论文
- 生物医学工程论文
- 神经学论文
- 口腔医学论文
- 医学论文范文
- 法医学论文
- 社会医学论文
- 整容医学论文
- 预防医学论文
- 医学检验论文
- 超声医学论文
- 放射医学论文
- 急诊医学论文
- 五官科论文
- 中西医结合论文
- 全科医学论文
- 康复医学论文
- 医学健康教育论文
- 病理学论文
- 基础医学论文
- 营养学论文
- 药学论文
- 环境法论文
- 刑法论文
- 版权法论文
- 国际商法论文
- 法学理论论文
- 行政法论文
- 民法论文
- 诉讼法论文
- 经济法论文
- 劳动法
- 海事海商法论文
- 法律史论文
- 公司法论文
- 民商法论文
- 婚姻法论文
- 票据法论文
- 森林法论文
- 商标法论文
- 宪法论文
- 新闻法论文
- 食品安全法论文
- 国际法论文
- 合同法
- 法律论文范文
- 知识产权法论文
- 税法写作
- 物权法论文
- 国际私法论文
- 国际海洋法论文
- 影视论文
- 广告设计论文
- 多媒体设计论文
- 纯艺术类论文
- 摄影艺术论文
- 美学论文
- 服装设计论文
- 动漫设计论文
- 室内装潢设计论文
- 戏剧论文
- 播音专业论文
- 舞蹈论文
- 环境设计论文
- 装饰与绘画论文
- 平面设计论文
- 化妆专业论文
- 戏曲论文
- 美术论文
- 电影论文
- 书法论文
- 环境艺术论文
- 工艺美术论文
- 绘画艺术论文
- 表演论文
- 导演/编导论文